李洱的小说创作实绩有目共睹,无论是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十佳长篇小说的《花腔》、得到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赞赏推荐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还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向以百科全书式的高知识容量,以及对时代人心的精准描摹为特色。
而在这本最新的文学笔记《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李洱化身为一位“文学侦探”,带我们潜入当代文学的现场,与汪曾祺、史铁生、莫言、格非等文坛大家展开一场“超低空飞行”式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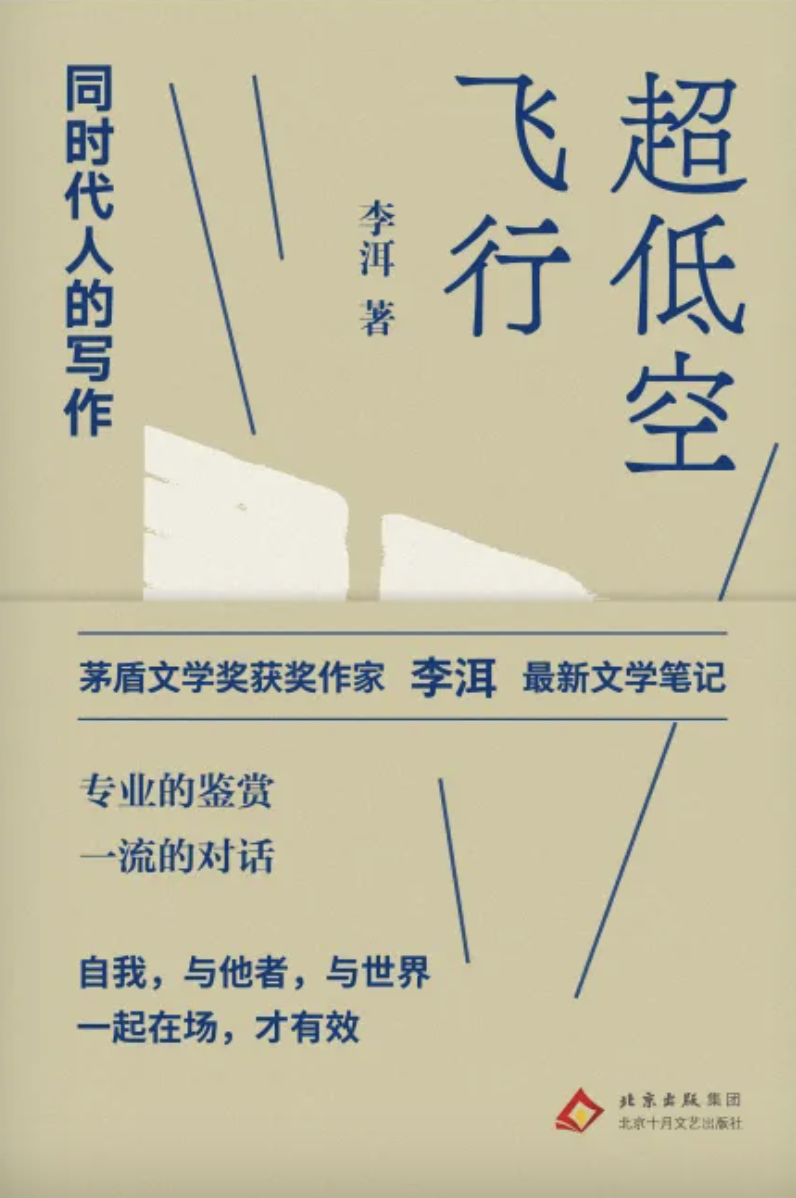
这本书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而是一次“贴地飞行”——李洱用他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洞见、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独特创作理念和个性,带我们读懂那些熟悉的作家和作品,也让我们看到文学背后的“人”与“世”。它不仅是一次对同代人的致敬,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读、如何写、如何与时代对话”的深度探讨。
文学不是孤岛,而是“一起在场”的对话。邀你到场,加入这次“超低空飞行”,一起靠近文学,靠近自我、他者和世界。以下为《超低空飞行:同代人的写作》节选:
小说即是对话
文/李洱
不同的场合,我总是听到人们说,小说家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对于生活中的作家个体来说,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其实,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让他同频共振,他也要力争同频共振。连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力争与时代同频共振呢,遑论他人?但是具体到小说创作本身,这个说法就值得推敲了。套用马克思的那个比喻就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白天“同频”,晚上不“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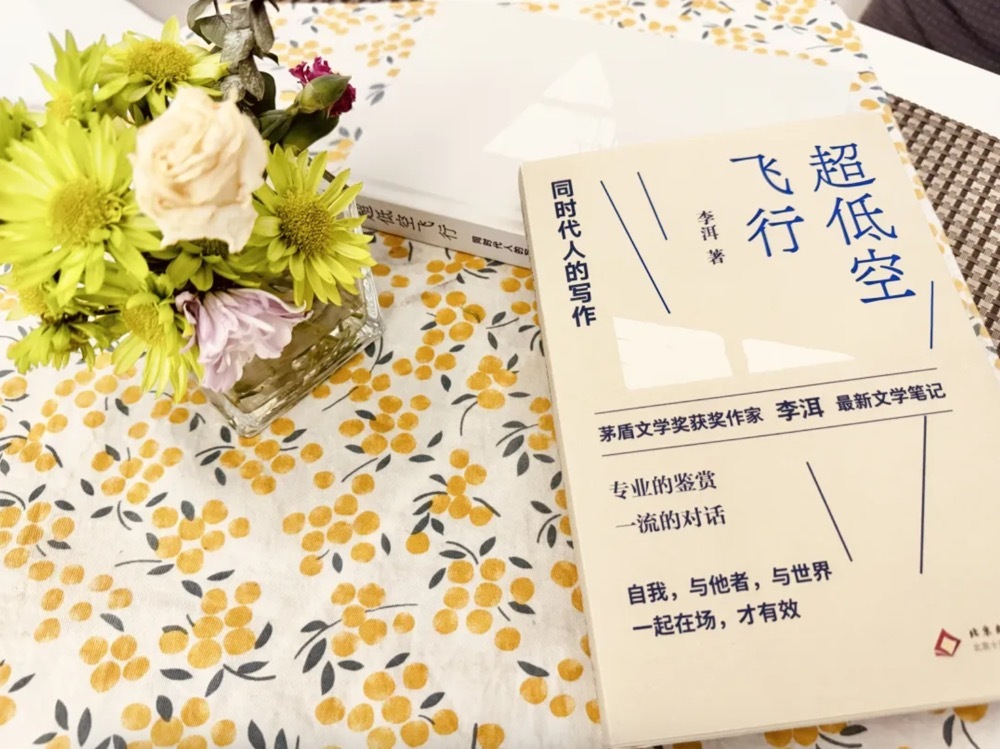
小说写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眼下的生活,而是虽然已经远去,却留在了脑子里的、对于经历过的生活的“活泼的印象”,也就是经验。“经验”的原始语义就是“经历”加“验证”。“验证”,就意味着你要不断回到过去,意味着对“故事”的重新发现以及重新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从来不说“小说要讲新事”,而是说“小说要讲故事”。辛亥革命过去十年之后,鲁迅才写下他的《阿Q正传》,正是这个道理。
所有的小说家,只要他不是存心应景,他的写作都会与现实保持着某种紧张关系。阿甘本在谈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特比》时,特别提到了写作者使用的工具:墨汁。阿甘本说:“墨汁,这用来书写的黑暗的水滴,就是思想本身。”阿甘本其实是想说,小说的注意力通常会集中于负面经验。这当然也是常识。小说之所以与时代构成对话关系,或者说,小说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它与时代构成对话关系,就是因为在小说家眼里一切尚未被主题化。这种对话关系越是紧张,它与时代的关系就越是亲密。在小说写作的意义上,“紧张”才是“亲密”的同义词,所谓的“亲密无间”其实意味着疏离,甚至背叛。当然,这也是常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耳闻目睹的景象。

所以,如果要问我,在你眼里,小说写作在这个时代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我会说,我倾向于认为,一定要与时代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当然应该落实到不同的层面,它既是与现实的对话,也是与传统的对话,更是与未来的对话。套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即是:“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着现在,我们倒退着走进未来。”
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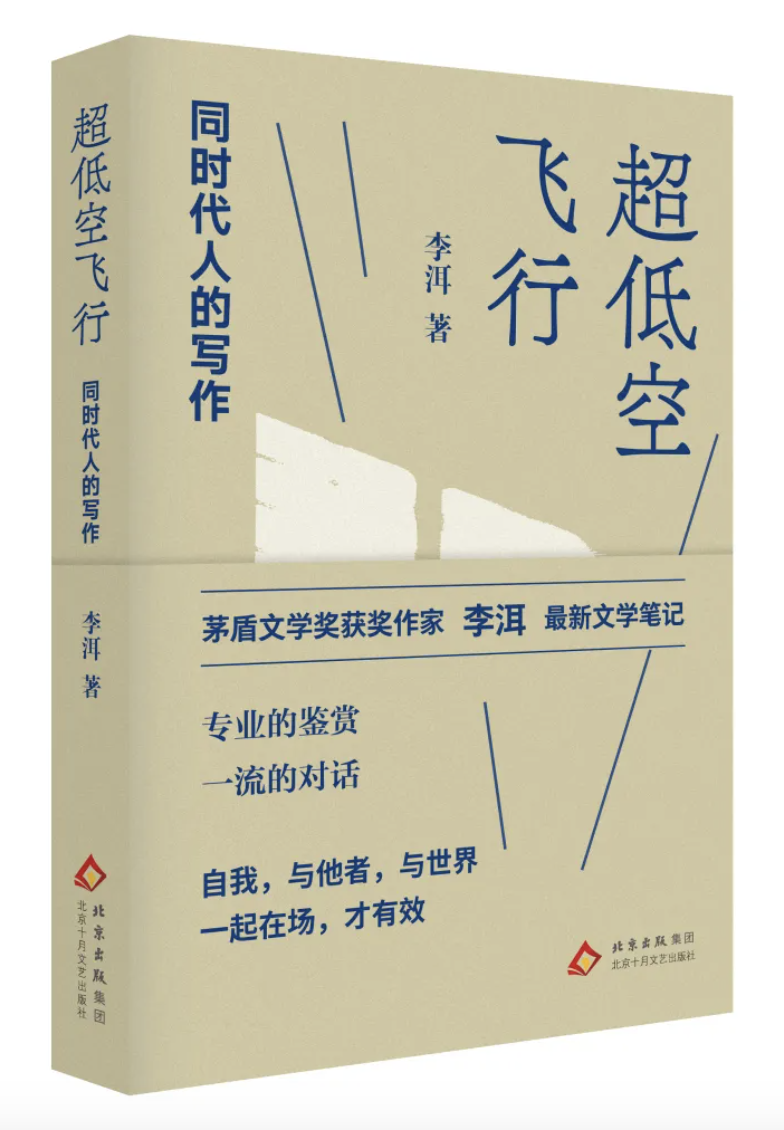
书名:《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
作者:李洱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2月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以批评者之姿态贴近、观察文学现场,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表达文学现场。
全书共分三辑。辑一、辑二眼光向外,着眼当代,阅人、阅世、阅文,剖析、解读同代人的创作,既包括对汪曾祺、史铁生、张洁等逝者的追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非、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以李洱之口与心,道出了他人所不能道的幽微与精彩。辑三回归自身,集中展示了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关于如何读经典、如何悟文心、如何写自身。若你对阅读与写作之得失有所希冀,此辑或许可以作一管窥。
互相观照,保持对话。置身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空间,与书本之上与笔墨之外的文与人,一起在场。
作者简介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等。《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应物兄》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