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2日,当代著名作家张楚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以“小说细节与县城宇宙”为题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第十八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李洱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张楚与他的文学成就。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继先锋文学后,一批小说家开始更多描写日常生活,他们将文化的世俗倾向与学科的专业倾向相结合,由此构成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向。作为描写日常生活的高手,张楚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成果颇丰。如其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云落》便虚构出一个县城,将形形色色的人物、林林总总的事物安插其间,在活动中移步换景地书写人物的命运和事物的变化,以现象学的方式呈现出云起云落的景观,构建起一个平凡但丰沛的世界。作为张楚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探索后的总结性成果,《云落》借助极尽繁复的细致笔触,使人物各自携带的生命信息、文化信息缓缓出现在读者面前,神形毕肖。此外,小说更将故事事实的陈述与道德价值的探讨有机融合,由此,这部小说构成了对90年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题材小说新的发展。

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张楚及其作品
张楚首先就“小说细节”这一话题展开分享。他指出,小说细节作为小说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渗透在人物肖像、语言、心理活动、外在行为、场景等描写中,可被视为小说是否成立的标志——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色生香的小说。由此,张楚提醒同学们关注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对细节处理方式的明显差异:一是密度的差异,如短篇小说的细节通常直接推动情节或揭示主题,而长篇小说的细节还兼具塑造人物、构建世界观等多重作用;二是选择的差异,短篇小说的细节更为谨慎私密,必须精挑细选,而长篇小说细节的选择相对自由,往往包含更多次要情节;三是深度的差异,短篇的细节受字数所限,往往点到即止,少有蔓延,而长篇的细节可以深入展开,提供更丰富的心理、风物等背景;四是节奏的差异,短篇节奏紧凑、速度迅捷,长篇则富于变化,能够灵活地加速减速,其间细节的处理方法也相应产生差异。总的来说,短篇小说的细节主要为核心服务,长篇小说的细节则更饱满丰富,对构建多维度的人物内心、社会关系等均发挥重要作用。

张楚在“小说家讲堂”
张楚进而介绍了细节描写的不同类型。传统意义上的细节描写分为肖像描写、环境描写、语言描写、表情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肖像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话本和西方古典主义小说中都很常见,最初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也常出现经典的肖像描写,但后续创作者多缺乏这种素描的耐心。在张楚看来,貌似简单的肖像描写恰恰最能体现小说家眼光的犀利程度、通感能力的强弱程度和对人物速写技能的高下。语言描写最常见的是对话,这是创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器。一些推崇“冰山理论”的小说家指出,对话不是无关紧要的嘘寒问暖,它可能语焉不详,但最终构成复杂的意寓,这种意寓在短篇小说中往往使故事内部分裂出强劲的诗性,如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等均是经典范例。此外,语言描写也常与表情描写、动作描写相结合,如人类的五官般缺一不可。成功的动作描写能充分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对此,张楚举阿城《棋王》中“王一生吃东西”的文段为例,分析其中动词运用的极致精妙。心理描写则是小说创作者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相关手段包括梦幻幻觉、内心独白、叙述者旁白、表情暗示、感官感受等。张楚认为,小说整体就如密度惊人的中子星,以有限体量承载着巨大艺术能量,这种独特文学形态也决定其细节并不停留于简单描画,而是包含丰富叙事意义的一处处“微观构造”。

海明威短篇小说
《白象似的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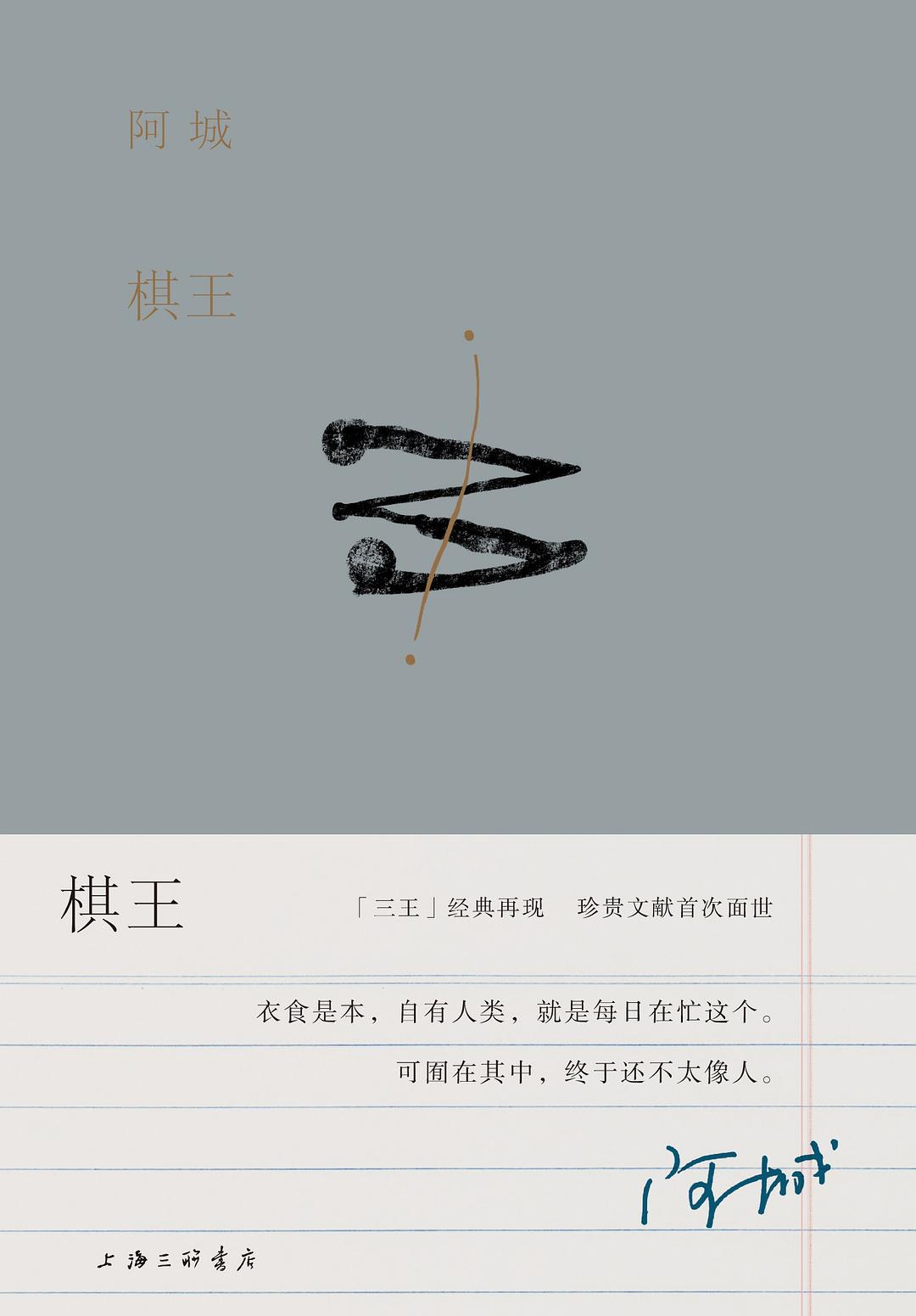
阿城短篇小说《棋王》
随后,张楚分析了小说细节的多种写法与效用。首先是多维度的沉浸式塑造,可以借助地理风貌、气候特征、建筑细节等塑造特定时空,如《百年孤独》中的漫长雨季、《巴黎圣母院》中的哥特式建筑;可以突破视觉局限,借助嗅觉、触觉、听觉等多重维度的交织,构建整体性的感官感受;可以藉由民族仪式场景还原等方式,赋予文本以历史纵深感。其次是构建动态的、特异性的“人格识别系统”,例如生理层面与行为层面(饮食习惯、方言修辞等)的描写均能暗示人物的价值取向。此外,也可以建立隐喻性的符号,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绿光”、《长恨歌》中的雕花檀木箱等,都彰显了长篇小说的细节美学。可以说,上述细节不仅承载着文学本体的审美价值,更构成了社会文化的记忆装置。例如,巴尔扎克通过书写1830年巴黎街道的招牌,无意间完成了对那一时期社会学的“标本采集”。类似的,张爱玲笔下老上海的电车铃声,同样是对彼时都市文化基因的编码与呈现。由此,小说得以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史册。

在深入讨论“小说细节”后,张楚继续就“县城”这一话题与同学们展开交流。在他看来,近年来网络盛行的“县城文学热”与真实的县城面貌存在一定距离,而更像是一种对上世纪90年代三线四线小城市风物的集体怀旧。张楚首先基于自己四十年县城生活的切身经验,回顾了近二十年来县城普遍经历的“大拆大建”,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县城逐渐脱离了破败、忧伤的旧有面貌。作为城乡的交叉点,县城内部的传统习俗与时代风潮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由此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风貌,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过程中的种种阵痛,伤痕和欢乐,在此都有着独特而深刻的展现。
由此,县城就像是中国现代发展的“微缩景观”,或者说是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中国的一处横切面,各种活色生香的人、最为基础的情感类型都能在此寻到,而他的很多中篇小说也正取材于县城现实。他分享了发生在自己身边亲友、同伴身上的许多故事,并指出,相对于城市,县城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如果将县政府比作恒星,星罗棋布的村庄就是围绕它运行的行星,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卫星,那些连缀其间的田野、树木、果园、河流、风、野狗、野兔、孤魂野鬼,可能就是散布在宇宙中的黑矮星、白矮星、黑洞甚至暗物质。在系统稳定、四季分明的宇宙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和其他宇宙里的人们一样,过着一种“被生活矫正过的生活”,他们的欢乐、痛苦、追逐,以及自己无法控制的坠落或堕落,都隐现着隐秘的欲望、复杂的选择与幽微的人性。因此,县城看似和平,内里实则波澜起伏,而当让你惊讶甚至惊艳的故事不定时发生时,能否抓住最具外延性的焦点就考验着作者选择的能力与眼界。

基于上述判断,张楚以自己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为例加以分析,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的重要性。如小说开篇对庭院环境的细节描写,不仅在最大程度上构建起想象的真实性,同时也是对人物关系的见证。此外,针对人物面临艰难抉择的心理描写片段,张楚重新还原了创作时复杂的心路历程,由此提出,写长篇小说需要着重处理两点:一是小说的结构,一是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后者,较简单的方法是从血缘和社会关系这两个维度考虑。人物关系编排得越紧密、越符合生活逻辑,小说自身的内部逻辑才能越真实可信,小说精神层面的探索才能获得更坚实的依托。
在讲座最后,张楚再次表明,即使是随心所欲创造的虚拟宇宙,也要通过无数的星系、恒星、行星、卫星和黑洞共同构建。在此过程中,造物者必须有绝对的自信,丝毫犹豫或迟钝都可能毁掉那些闪光的星系。另一方面,每个造物者的特性偏好都可能影响宇宙的疆域与形状,因此被构建的宇宙终归是可疑的、主观的,但确定的是,在小说家塑造人物、推进叙事时,在小说家于自己的逻辑范畴之内讲述宇宙的卑微或伟大、光明或黑暗时,正是那些有意或无意间写出的饱满的、闪亮的、诗性的、具有生命力的细节,为我们有限的感官带来无限的思维发散,并提供独属于小说与文字的巨大幸福感。
演讲结束后,李洱教授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场讲座内容极为丰富,确如张楚所言,即使是一处微小的细节,一旦被写活,也可能映照个人的生理感受甚至更为宏大的家国命运,并构成普世意义的“人间故事”。同学们就如何为地域诊脉、如何理解小说中的社会关系、如何权衡方言在写作中使用的比例、如何处理县城与城乡关系等话题积极提问,张楚一一作出细致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提问互动环节

张楚为同学们签名
撰稿:时悦驰
摄影:秦雨洁
编辑:鲁沛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