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9日,当代著名作家弋舟走进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以“与当代经典相遇”为题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第十一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李洱教授主持。

弋舟在“小说家讲堂”
讲座开始前,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道,弋舟先生是七零后作家中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李洱教授援引罗兰·巴特给安东尼奥尼信中提到的“艺术家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是警觉、智慧和脆弱”来形容弋舟的小说。弋舟近年出版了可以称为“人间纪年”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包括《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辛丑故事集》等,写出了当代人在这个变动不居时代的精神生活。弋舟的小说写的多是一代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如何参与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进程,他的小说人物仿佛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和强烈的自我质疑,具有真正的诗意,表达了一种有关沟通、信任、相互搭救的艰难的诉求,多部小说都可以当成创意写作的教材来分析。

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弋舟及其作品
随后弋舟开始演讲,他的题目为“与当代经典相遇”。说起“经典”,最令人耳熟能详的无疑是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十四条定义。弋舟回想起世纪初在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段落:
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弋舟以与主持人李洱进行现场对话的方式提到,彼时他刚开始创作小说,与这段文字的相遇恰与他的日常经验与精神生活对应。这段出自李洱中篇小说《午后的诗学》的文字,恰恰印证了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第一个定义——“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读者在阅读经典时感到似曾相识,这种似曾相识不仅体现在它所描述的景象是我们的日常经验,还因为它的描述与修辞在我们所投身的文学传统之中其来有自,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是保守的,是在顽固地赓续着某种伟大的传统。一部经典即使是新作,也不会和我们既有的修养与经验构成冲突。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关于经典的14条定义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这是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又一定义。通过回顾阅读李洱《花腔》的经验,弋舟认为自己在不同的阶段会和作品形成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欣赏与赞美,也可能是因为对阅读时的判断产生动摇而形成某种对抗的力量,从而在反驳李洱、反驳《花腔》的过程中阶段性地塑造自己。经典作品正是有着这样的功效,读者在与其的张力关系之中确立自己。
随后,弋舟讨论了“当代”这一命题。倘若以李白为例讨论经典,自然会容易得多,也合法得多,他已被时光加冕,这意味着“经典”事实上是一个高度依赖时间的概念。诗与远方好过就近的日常,这似乎是人的一个基本思维定式,然而对于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性命名始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被同代之人阅读、谈论与批评是其成为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一个好的作家理应具有追求经典并成为经典的抱负,同时也理应培植自己发现和指认当代经典的愿望。在弋舟看来,这关乎胸襟,也关乎能力,关乎我们对自己审美的信心与勇气。

关于“相遇”,弋舟以格非创作于1994年的短篇小说《相遇》作为文本抓手。《相遇》这篇小说以极大的格局,书写了两个狭路相逢的文明。1903年的初夏,一支由英国人、印度的锡克人和廓尔喀人混编而成的远征军侵入了西藏,故事由此展开。这篇小说以史实为背景,体现出格非作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敏感,这份敏感让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捕捉到了这一事件的深长意味。而从历史真实入手找到虚构的方法,是弋舟作为一名写作者,在技术方面格外看重《相遇》这个短篇小说的原因。
小说有义务为读者还原出一个物理世界,这种还原非但是小说伦理之一种,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写作技巧,驾驭得当的话,非但能令虚构之作显得理直气壮,还可以使作品弥漫着某种巫术一般的逼真感,令作者在创作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相遇》中出现了一系列动植物的名称,有些物种读者闻所未闻,但当它们遍布于小说之中,就使得作者以一种博物学家一般的风度一一替读者指认那方绝对客观真实的现场,由此为小说营造出某种堪称专断的、不由分说的氛围,这种陌生、异质不在读者经验当中,成功地说服读者进入小说的世界——它是真实不虚的存在。经过重重转述获得未曾经历的知识是一名小说家的工作方法,这也是弋舟心目中一流小说家工作时的模范状态:严谨、勤勉、较真、恪尽职守,从物理世界不厌其烦地为自己的虚构之书搬运着一砖一瓦。

在搭建了坚固的物理基础之后,小说家还要凭空跃起。弋舟带领同学们深入《相遇》的文本之中。格非在密集的、紧张的甚至枯燥的时间表里,书写出逆向的缓慢。传教士让中国官员观看显微镜的情节,从视觉的刺激转化成对于时间的惊悚,由此在小说中从始至终地营造了一种惆怅的凝滞感。小说写两种迥异的文明的相遇,两种文明正是在不同的时间感中构成了相遇的对手。
《相遇》写空间亦别具一格,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真实地名营造出一种逼真的史实感。小说的结尾有如神来之笔:侵略者失败了,他带着西方文明的傲慢,在西藏的雪域高地遇到了空前的失败。失意的侵略者回忆起曾与大住持就地理常识发生的争吵:
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
格非给出了如此具体的、详实的,甚至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准确的空间的指认,最后用这样一个东方的修行者的世界观做了极为有力的,甚至极富诗意的、极富文学性的反驳,同时这也是这一对相遇的文明对撞出来的结果。在这个结尾中,格非颠覆了整部小说苦心营造的一切真,也由此使得小说最终抵达了虚无。
弋舟表示,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能天然地从这些小说当中感受到其散发的光芒。他提示同学们,从《相遇》《午后的诗学》这样的短篇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位成熟小说家运思的方式,还能从中训练自己——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或者一个好的阅读者——所应具备的更为复杂的对历史和文明的宏观思辨能力。小说本身篇幅很短,描写的却是大事件,读来并不空泛,弋舟认为这就是一流小说家的能力,也是经典作品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文学奖项而言,格非、李洱等作家获得茅奖,已经完成了“经典化”,但在此之前,他们就奉献出《相遇》《午后的诗学》这样的杰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拒绝与当代文学的相遇?
弋舟对文本的分析鞭辟入里,对当代小说家的创作见解独到。同学们就弋舟小说《等深》的人物塑造、短篇小说创作中真实经验的切入等问题进行提问,弋舟一一回应。讲座在愉快的氛围里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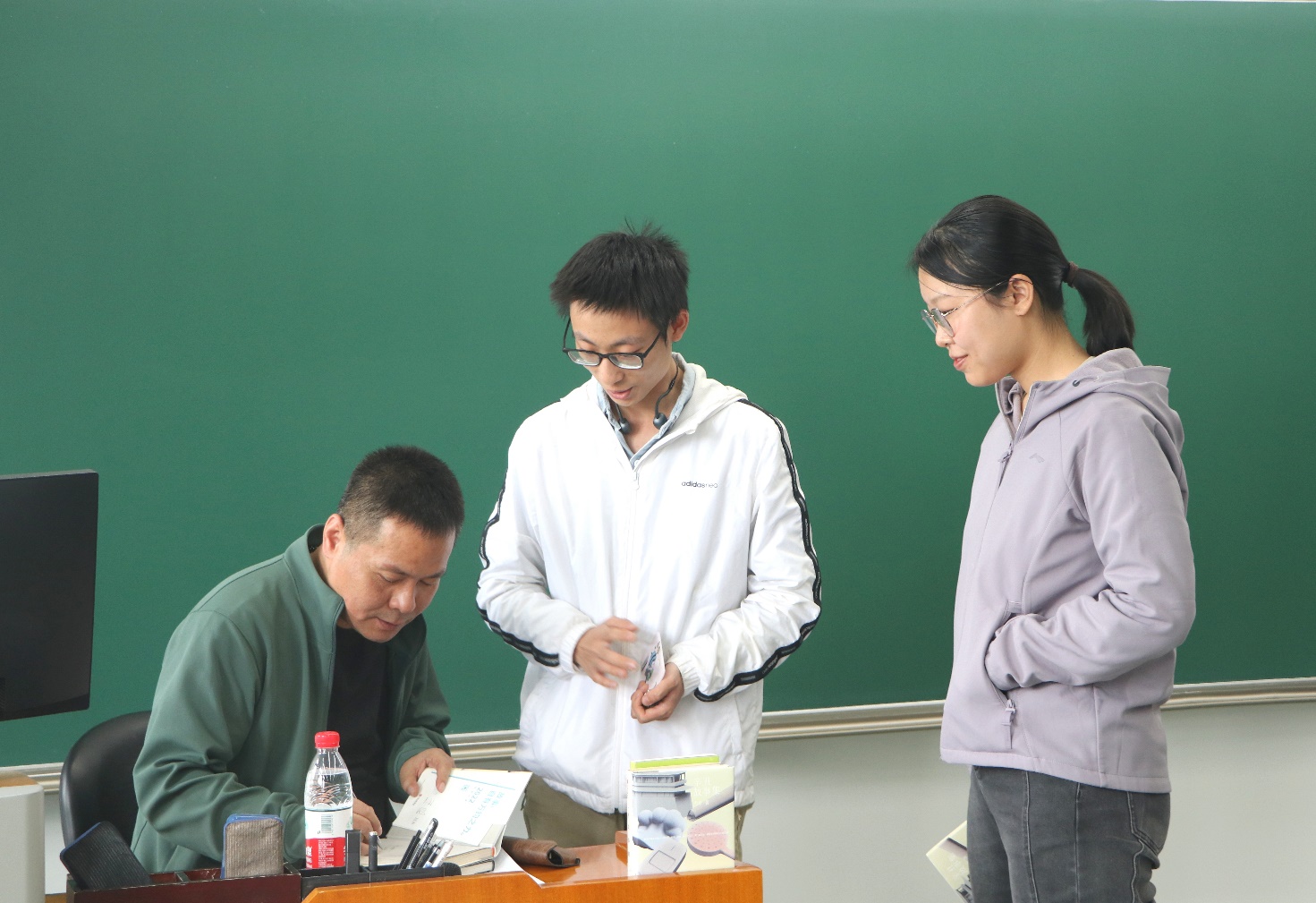
弋舟为同学们签名


同学们踊跃提问
撰稿:潘舒婷
摄影:陈晓彤
编辑: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