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一枫在“小说家讲堂”
2023年11月21日,当代著名作家、北大中文系系友石一枫做客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以“把世界讲成故事,让故事成为世界”为题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是“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石一枫及其作品。李洱教授指出,在老舍、王朔之后,石一枫的写作构成了北京文学的重要风景。批评家称石一枫的描写对象是“新北京人”,此言得之。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北京人乃至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描写这种变化,如何描写北京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命题。以《世间已无陈金芳》《飘洋过海来送你》两部作品为例,李洱教授表示,石一枫的小说能够为这一命题提供极佳的写作范例与广阔的阐释空间。最后,李洱教授赞扬了“把世界讲成故事,让故事成为世界”这一题目所表现的雄心壮志,并鼓励所有热爱写作者也抱有这样的雄心——“我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容纳整个世界”。

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石一枫及其作品
石一枫以如何理解“世界”入题,对李洱老师的介绍进行了回应。石一枫认为,时代的变迁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有所变更。曾经“世界”在我们的语境中指向外国与西方,我们则是一个外化于遥远世界的观察者。然而,在他看来,“世界”是人类整体的世界,亦是我们巨大的生存环境,我们是内化于世界之中的。诸多的“城市”则是“世界”的重要节点,自己的写作就是“站在北京看世界”的写作。正如威廉·福克纳与美国南部的小镇,保罗·奥斯特与纽约的布鲁克林,伊凡·威尔士与苏格兰的爱丁堡,王安忆与上海,老舍与北京……作家的作品和城市构成了相对紧密的互文关系,或是作家书写了城市,抑或是城市写就了作家,总而言之,城市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
接下来,石一枫用相互对立、相互关联的“概念”提纲挈领,展开了他的演讲。石一枫指出,一个作家成熟的过程,就是找到对自己而言重要的概念的过程。在创作中,作家专心致志地处理这些概念,处理的方式变得更深入、更丰富,就是作家写作进步的象征;如果能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新的概念,则会对写作带来大的飞跃。课堂上,石一枫为我们分享了自己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六对概念。

第一对概念,是“现实”与“故事”。
石一枫指出,作家如何处理故事与现实、故事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小说的整体气象。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认为,故事需要还原世界;另一些学科则认为,故事需要总结世界。然而,在石一枫看来,故事本身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观念。观念是新观念,故事就有意思;观念是旧观念,故事就没意思。“把世界讲成故事”,揭示的就是故事与现实的关系——有还原、有总结,更有作家在其间的变形与加工,蕴含着作家独特的观念与价值。《悲惨世界》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若是只有还原与总结,小说中便只有芳汀而不会有冉·阿让,冉·阿让这样理想型的人物,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理念对所处时代与环境的变形和期许。
故事和世界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小说的主题,还会影响小说的笔调和质感。石一枫生动形象地把对小说质感的要求描述为“肥瘦得当”,然而,在一众小说中也有例外。以陕西作家杨争光的写作为例,他的小说质感尤其“瘦”,这一特质对应的是他对故事与世界的看法。他的小说高度强调对世界的总结,在总结和凝练的过程中,作家近乎把小说写成寓言,篇幅则短,质感则“瘦”。由此可见,故事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小说的诸多方面。
第二对概念,是“熟悉”与“陌生”。
熟悉与陌生的关系是小说创作中难免会考虑的问题。在石一枫看来,熟悉是创作的必要工作,无论是通过理性的认知,还是通过感性的想象,在创作一个陌生的题材前,作家都需要将其变得熟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作家都是自传型的作家——只会讲自己的故事,不会讲别人的故事,在切身的生活经验书写殆尽之后,作品就变得空洞无味。因此,石一枫指出,处理从陌生到熟悉的能力非常重要,讲好别人的故事才是一种真正的才能。
石一枫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写作之初,他的小说中都有自己。后来,小说中只有一半是自己。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一半是陈金芳,一半是“我”,“我”去观看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当时,用“熟悉”去理解“陌生”,是石一枫处理二者关系的方式。这一方法也被其他作家所采用,以毛姆为例,《刀锋》中的拉里是维特根斯坦的化身,毛姆不直接书写维特根斯坦,而是用“我”这一角色去观看拉里,从而实现了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搭桥”。而后,写下《借命而生》这个警察与逃犯的故事之后,石一枫才敢于把自己称为“小说家”,因为他有能力完成从陌生到熟悉的跨越,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故事。
石一枫还提醒大家,了不起的作家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把熟悉讲成陌生。他指出,惊艳的小说往往有一个特点——讲的是熟悉的日常生活,却显得惊心动魄、荒诞不经。一个对世界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念和看法的人,才能够把熟悉讲成陌生。正如卡夫卡将坐办公室的小职员写出深度,又如鲁迅将千百年来中国人熟悉的世界变为陌生。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找到新意,从陌生写到熟悉,再把熟悉写到陌生,这是一个反复回旋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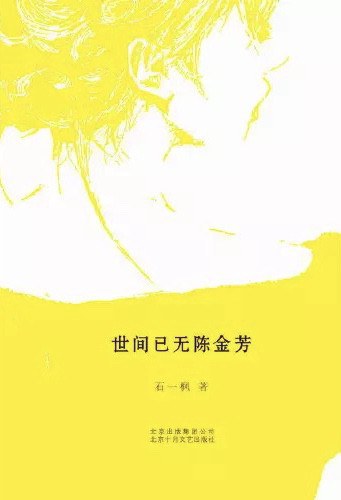

石一枫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借命而生》
第三对概念,是“专有知识”与“文学特质”。
当今的世界,专业分工越来越复杂,每个专业、每个学科都可能成为作家的写作素材。作家在创作一个现代社会的主题时,也难免触及到专业知识的问题。那么,作家应该如何处理专业知识和文学特质的关系?在石一枫看来,小说不能仅仅传递专业知识,不能局限于描写一个行当的门道,而是要让专业知识服务文学特质。
石一枫提到,作家的“知识膨胀”在当下变得非常明显。对于这些作品,作者和读者都要进行一个检验:看完之后是否既能了解作品中的门道,还能记住作品中的人。以李洱的《应物兄》为例,石一枫指出,《应物兄》是一部知识含量极其庞大、极其艰深的小说,然而读者在读完之后能够深深地记住应物兄这一角色,这便是小说的出色之处。石一枫强调,在知识非常个性化、专门化的今天,处理“专有知识”和“文学特质”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第四对概念,是“作者”与“读者”。
在石一枫看来,文学的接受非常重要,作家应当重视读者的感受,将读者视为文学中的重要一环。石一枫谈到,自己有十几年的编辑经验,因此常常在创作中用编辑的眼光、读者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注重读者的写作伦理要求作家创作通俗化、民间化,因此,石一枫更加倾向用浅显的、晓畅的、可读性强的方式写作。不过,用这种方式写作更需要注意“一言难尽”。小说的每一段都清晰晓畅,但看完应当给人以“一言难尽”之感。衡量一个题材值不值得写,也应当看是否能在其中找到“一言难尽”之处,并围绕此处去做文章。

第五对概念,是“表形”与“表意”。
石一枫首先为这一概括做出题解。“表形”和“表意”,也就是形象化的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语言,在他看来,南方和北方的写作就有不同的特色。石一枫基本用北京话写作,北京话的特点是口语和书面语的高度一致。这种语言长于“表形”而短于“表意”,能够很好地描绘动作与形象,却在描写逻辑与思想之时力有未逮。以老舍为例,他写旧北京人能够花样百出,但写新北京人的社会思想时,就在表述能力上展现出短板来。
北京作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啰嗦”,写作时往往泥沙俱下,为了追求气势而失去了文字的准确性。相比之下,或是因为需要在创作中将方言母语转译为普通话,南方作家这一过滤和梳理的过程让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更加精炼、老道。石一枫提出一个自我省思,作为北京人,如何发挥口语母语的优势,如何避免口语母语的劣势,都是需要注意的命题。为此,他会放慢写作速度,对文字多加斟酌。他提醒所有创作者,语言习惯是把双刃剑,应当看到自己的语言习惯造成的问题。
第六对概念,是“简单”与“复杂”。
对这对概念,石一枫解释道,“简单”与“复杂”是关乎写作心态的问题。在他看来,今天的小说是越复杂越好。十九世纪的人类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复杂的遗产,如瑞士表、交响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都是高度复杂、高度精密的。时间的齿轮转到二十一世纪,小说比起当初只会更复杂,不会更简单。如今,小说不仅要处理情节的复杂,还要处理人物的复杂、思想的复杂、社会问题的复杂,不一而足。多个层面的结合,让小说的复杂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写小说高度强调“算力”,因此也必然是耗神的。
与此同时,石一枫也强调了简单的重要性。他指出,写小说的状态最好是“思想复杂、心地单纯”。好的小说家的特质在于,脑袋中思考的事情天花乱坠,但有时候却能单纯得像个孩子。
讲座最后,石一枫真挚地说:“每写一部长一点的作品,这些概念都会出现。琢磨好了,写小说的过程就相对会顺利。我觉得这是大家也会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对大家的写作和研究有所帮助。”同学们对这场干货满满讲座致以热烈的掌声,并踊跃地向石一枫提问。在提问环节中,石一枫就小说与时代的勾连、小说中不同人物的价值、小说的幽默等问题都做出了精彩的回答和阐释。



同学向石一枫踊跃提问
李洱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高度评价了石一枫对问题思考的深度。李洱教授指出,石一枫所提炼的文学创作中的六对概念,涉及的都是创作中遇到的根本问题,如“写作不是还原与总结,而是重构与发现”、“自传型作家的转型”等。这些根本问题,充满着进一步展开讨论的空间。此外,石一枫的许多话题都带有深刻的自省性,如他对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讨论。讲座的最后,李洱教授热情地邀请道:“我们欢迎他有时间继续来讲课!”

讲座后,石一枫为同学们签名
随后,蔡恒平、崔曼莉与同学们就村上春树的写作与阅读展开交流,围绕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情感经验与写作实践、小说的“治愈性”等话题进行了诚恳的讨论。
撰稿:陈绚
摄影:陈晓彤
编辑:雷宁

